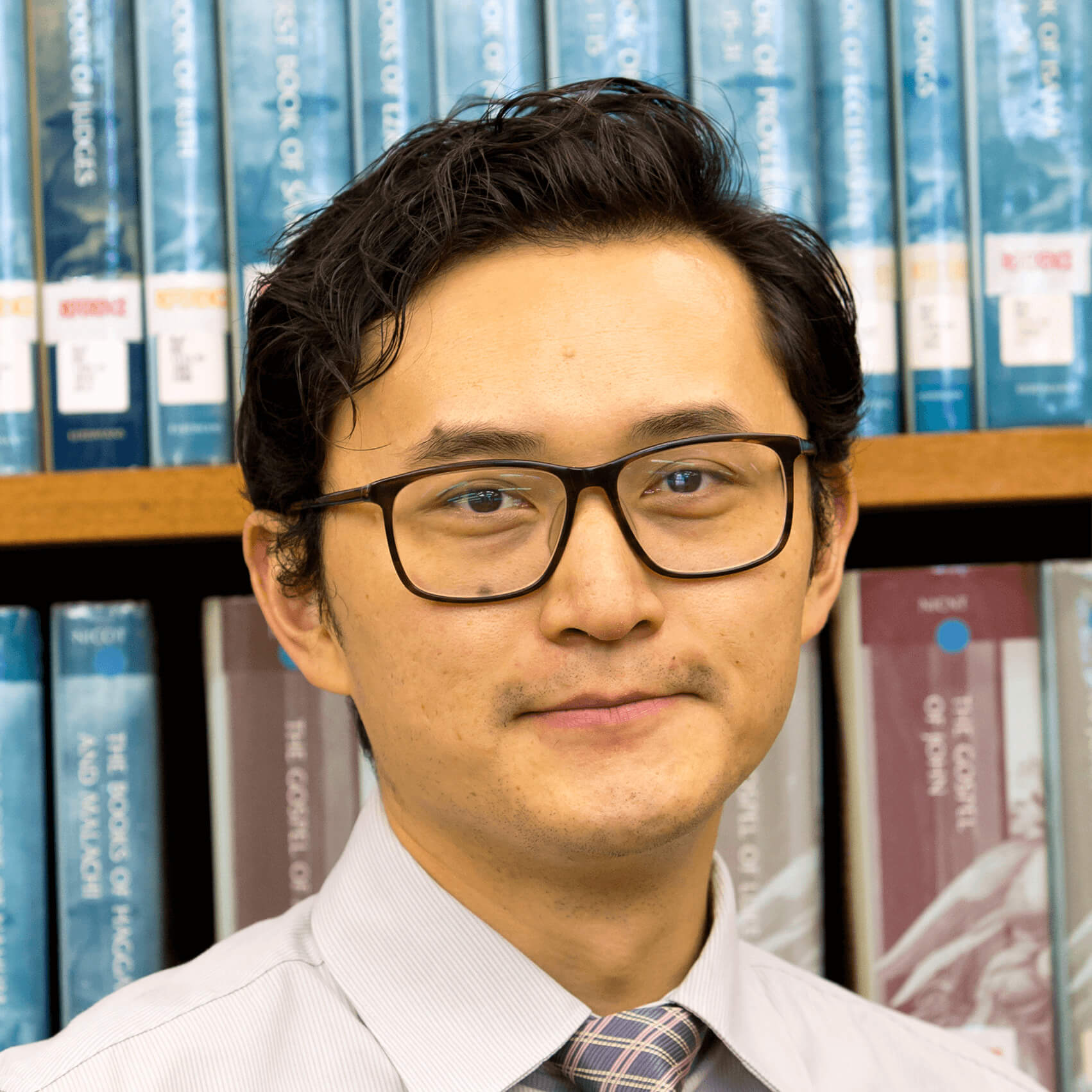【新老師介紹】長洲.柏林.長洲/陳韋安

九年前,二十四歲的小伙子與太太結婚不足一個月,就入住當時仍是已婚宿舍的莊漢樂樓,建立新婚後第一個家。我們是當時學院年紀最輕的夫婦。然後是建道三年難忘的生活,與許多校友一樣的經歷,笑過,哭過,磨練過,認識了上帝更多,結識了一班終生戰友,發現上帝擺在我們前頭的使命。
畢業後,我們離開香港,遠赴陌生的德國。第一年花上所有時間學習德文,適應環境。太太凱玲在柏林宣道會事奉,當時我們都是初出茅廬的神學生,要獨力承擔整個宣教工場,只能戰戰兢兢地事奉下去。
第一年生活安頓過後,我在德國的神學生涯正式開始。一星期五天的神學研究,周末在教會事奉,閱讀、思考、寫作、事奉,閱讀、思考、寫作、事奉……從不間斷的。每天從一百年前的書堆中思想上帝,在大學旁聽一些神學科目,主動尋找可討論的對話夥伴,同時又面對眼前活生生的教會,讓我可以在神學思考與教會現況中畫出一條彼此可依據的量度。外國的體驗,宣教工場的事奉,與內地學生相處,這些經歷,這種思考琢磨,都不是在香港容易獲得的,實在非常寶貴。六年的光陰就是這樣渡過。我們第一條白頭髮都是在德國長出來了。然而,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所獲得的成長經驗極其豐富,難能可貴。
三年長洲,六年柏林,兜兜轉轉的,又回到這個小島。8月7日,和太太拖著行李,從機場到中環,從中環到長洲碼頭,從碼頭又回到神學院。和太太拖著手,久違了的酷熱高溫,路途盡是密密麻麻的長洲村屋,似乎忘記了路,我們卻能隨著直覺一直一直往前走。第一個的竟然是蘇師父。我們都不禁大聲地喊叫:「蘇師父!」回到神學院,由從前的莊漢樂樓變為現在的「三十一號」,心裡感覺很奇妙。很多都是陌生的,但其實又是熟悉的。然而,面對熟悉的的環境、熟悉的人物、熟悉的長洲炎夏,卻又不能一時間完全適應過來。
因此,回到香港後的幾個星期,生活上仍有許多未能適應過來。尤其是面對在建道前面的事奉,心裡其實有點緊張。9月2日上班前的一個晚上,收拾預備明天上班的東西,我問太太:「我們的《生命聖詩》在哪裡?」畢業後,我們把《生命聖詩》帶過去德國,卻一直沒有機會拿出來使用,也很久沒有用廣東話唱詩歌了。翌日早上開會,建道同工們有唱詩靈修的時間,我打開手中這本《生命聖詩》,與同工一起開口唱詩。那一刻,我才發現,過去建道三年的回憶,那留下來、傳承下來的,實在遠遠超過三年,並且已經不知不覺影響著我日後的生命。於是,在母校再次翻開《生命聖詩》唱詩歌,先前許多的不適應都盡消除。「其實這不就是建道嗎?我緊張甚麼?」我心裡想。那刻,我才發現,在外留學的六年,其實只是簡單的中途站。我又回到建道了。
回到建道,很享受每次與人交談的機會,無論是老師、同學或是同工,每次交談都是很寫意的。我感到,上帝似乎要我在建道繼續學習過往還未學完的功課,只是換了一個角色。還記得早前的屬靈操練營,我第一次以老師身分參與營會,第一次從老師的角度體驗這個屬靈操練營,感受非常深。在營會裡,幾個老師在教師營舍住一起,間中聽見陳耀鵬牧師、何啓明牧師幾個牧者前輩的風趣對話,實在感受到過往七十年代的建道情懷;當我走在廖博、蔡牧、張sir身邊時,[1]卻又是另一種九十年代建道的使命感。然後,當我回到自己帶領的關心小組,面對比自己更年輕的神學生,又是另一種全新青蔥的感覺。建道,不斷孕育著一代又一代人。時間過去,年代過去,身分在轉變,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建道的精神與價值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延續著。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想法,相同的召命。
因此,於我來說,是老師,還是學生?其實,又有何分別呢?我們都是在人生不同階段領受著相同的召命,努力面對上帝為我們預備的挑戰。
我是這樣面對前面建道的事奉。(當然,被同學誤會是同學的情境仍在發生中……)
註釋: [1] 編按:「廖博」即廖炳堂博士,「蔡牧」即蔡少琪牧師,「張sir」即張雲開老師,而前文提及的「蘇師傳」,即事務部同工蘇揚喜先生。
原載於《建道通訊》173期,2013年10月,頁18-19。
作者簡介
陳韋安
神學系副教授
國際學院副總監
最新文章
【畢業生分享】重新導航──導引一生的神 / 王雅君
2026 年 1 月 1 日
【畢業生分享】屬靈導引的生命體會——與上主同工的旅程 / 黃芳
2026 年 1 月 1 日
【校本部學生分享】重拾與主同行的節奏——依納爵神操旅程反思 / 鄭家恩
2026 年 1 月 1 日
編輯精選
[電子書]困境與抉擇:「建道研究中心30週年誌慶」跨學科研討會論文集/廖炳堂、倪步曉主編
2025 年 1 月 2 日
從梧州到長洲:建道神學院125年的挑戰與恩典 / 陳智衡
2023 年 10 月 1 日
微小教會的見證/高銘謙
2023 年 6 月 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