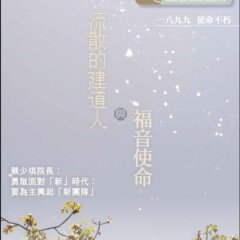【老師專欄】沒休止的敬拜—為何要研讀崇拜學? / 朱裕文
研讀崇拜學的目的是甚麼?不少同學以為學院設立這學科的目的,是為未來會的需要作準備,故此在教牧神學課程中,加入一些實用學科,讓同學他日到工場事奉時,對教會崇拜有基本的概念,有助牧養和領導教會。崇拜學無疑是為裝備學生而設的教牧神學科目,但是這課程所涵蓋的,絕不純屬一套知識,它更是由概念到實踐的一門學科,因此在課程設計上,可說是理念與功用兼備。
現代敬拜的支持者認為,「現代形式的敬拜更容易摸著現代人的心靈,因此沒有所謂正統敬拜與現代敬拜,只有真實的敬拜與不夠真實的敬拜;只有深入的敬拜與不夠深入的敬拜。」[1]這是一種極受後現代文化影響的思想與趨向,當中強調沒有「正統」的模式,只要求「真」,只求在敬拜中享受個人的自由與釋放,這種想法確實影響今日許多信徒。究竟「真」的標準是甚麼?我們應該如何判斷?
從歷史角度分析,禮儀神學強調神的道是信徒敬拜的準則,在敬拜的行動中要表現出正確的教義(right doctrine in action),這是根據十四世紀Prosper of Aquitaine所說的名言:「禱告的法則就是信仰的規條」(Lex orandi lex credendi〔the rule of prayer is the rule of faith〕)。[2]我們要知道,禮儀與敬拜者的心靈要互相配合,才能達至禮儀與信仰生命一致。過去多個世紀以來,禮儀被指為僵化和規條化,是因教會未盡全力教導信徒,以致他們的屬靈生命停滯,缺乏生命上的操練,如此在敬拜時便未能體現真理,只依隨形式進行敬拜,。故此,我們相信假如禮儀運用得當不但不會使敬拜僵化,反而能夠深化信徒的屬靈生命。
在真理指導下的敬拜,並不會成為心靈的桎梏。貝斯(Harold M. Best)在他的近作《不休止的敬拜》(Unceasing Worship)中,提出敬拜的生命勝過任何形式,敬拜就是不停地傾倒生命,而個人的敬虔與聖潔就是建造在這基礎上。貝斯不排斥一切敬拜的禮儀,或選擇自由敬拜的模式;但強調不休止的信心才會生發持續的敬拜。貝斯所主張的敬拜,是形式背後應有真理作為基礎,不讓人以自由做藉口,放棄以真理為基礎的敬拜。
人的靈命是在心靈裡活動的。韋富理(John Witvliet)以氣壓計解釋敬拜,認為敬拜仿如屬靈的氣壓計(worship as a spiritual barometer),可探知人的屬靈景況。這種論調就好像在早期先知的著作中,往往以領導者的敬虔去闡釋以色列民的屬靈狀況,從而顯示以色列民整體的屬靈溫度[3]。因此無論在什麼時代,關注心靈的敬拜都是最根本的。
羅理(H.H. Rowley)在Worship in Ancient Israel:Its Forms and Meaning中便開宗明義指出:「敬拜的素質出自心靈,多於從形式方面流露,因敬拜是屬於心靈的,而非僅屬於行動。」[4]但我們應該同時切記,羅理的研究也顯示,神設立的敬拜儀節,其意義是曉導以色列人的心靈,使他們依照神的訓示敬拜。因此,神學知識有導引的作用,指示我們不能單憑感覺去敬拜,因為敬拜需要真理作基礎,真理能塑造教會群體的生命,正如神當日用律法和禮儀指導以色列民,使他們依從神的吩咐來敬拜。
二十一世紀的傳道人,正面對牧養上許多議題。崇拜學的設立,就是為教會的敬拜和牧養尋求真理的立場與思路,讓信徒能循著真理,以正確的信仰方向敬拜神。
註: [1] 夏忠堅:〈一場敬拜的對話〉,<www.ccea.org.tw/ceo/Functioncode/Publish/ focusnew.asp?Method = Movel_ast&type>(2003年3月19日下載) [2] “Speaking from an explicit Reformed perspective "worship inevitably follows theological conviction .... We believe that good theology must produce good worship ... defective theology yields inferior or inappropriate forms of worship” D.G. Hart and John R. Muether, With Reverence and Awe:Returning to the Basics of Re- formed Worship(New Jersey P&R Publishing 2002),13。最值得憂慮的是,牧者在崇拜神學上沒有尋求神學定位,只追隨風尚。 [3] John Witvliet, Worship Seeking Understanding:Windows into Chris- tian Practice(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3)25-30。韋富理分析以色列民早期的敬拜(參歷代志上下,以斯拉記,尼希米記及以斯帖記)時指出,無論在祭禮、節期與聖約禮儀(covenantal-renewal rite)方面,以色列民族的政治、道德及屬靈情況都影響著他們的敬拜。以士師記為例,那時以色列沒有王,於是許多代的以色列人都追随外邦人敬拜假神(士二(10〜19;十七章)。 [4] H.H. Rowley,Worship in Ancient Israel:Its Forms and Meaning(London:SPCK,1967),3.“For I am not so much concerned with the final interpretation a rite came to be given as with its meaning the worshipper at the time of his worship。The Old Testament covers a very long period,and neither the forms nor the spirit remained unchanged throughout this period。”
原載於《建道通訊》141期,2005年10月,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