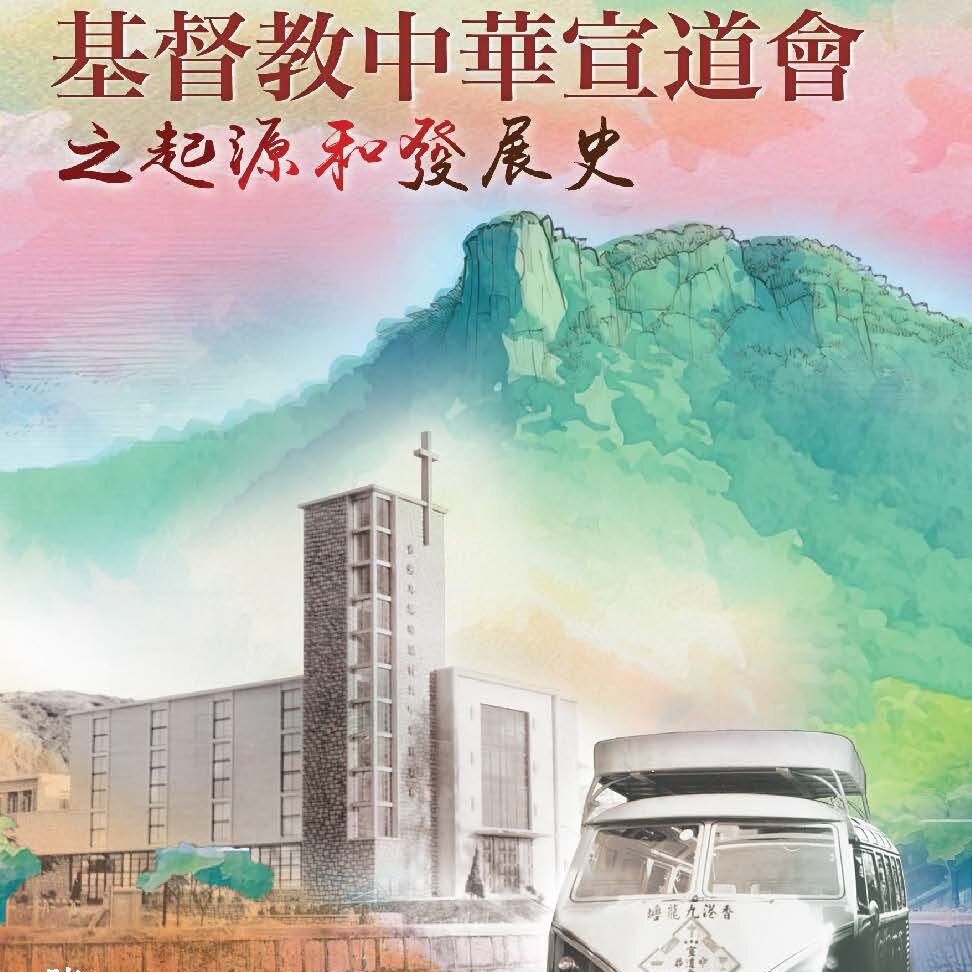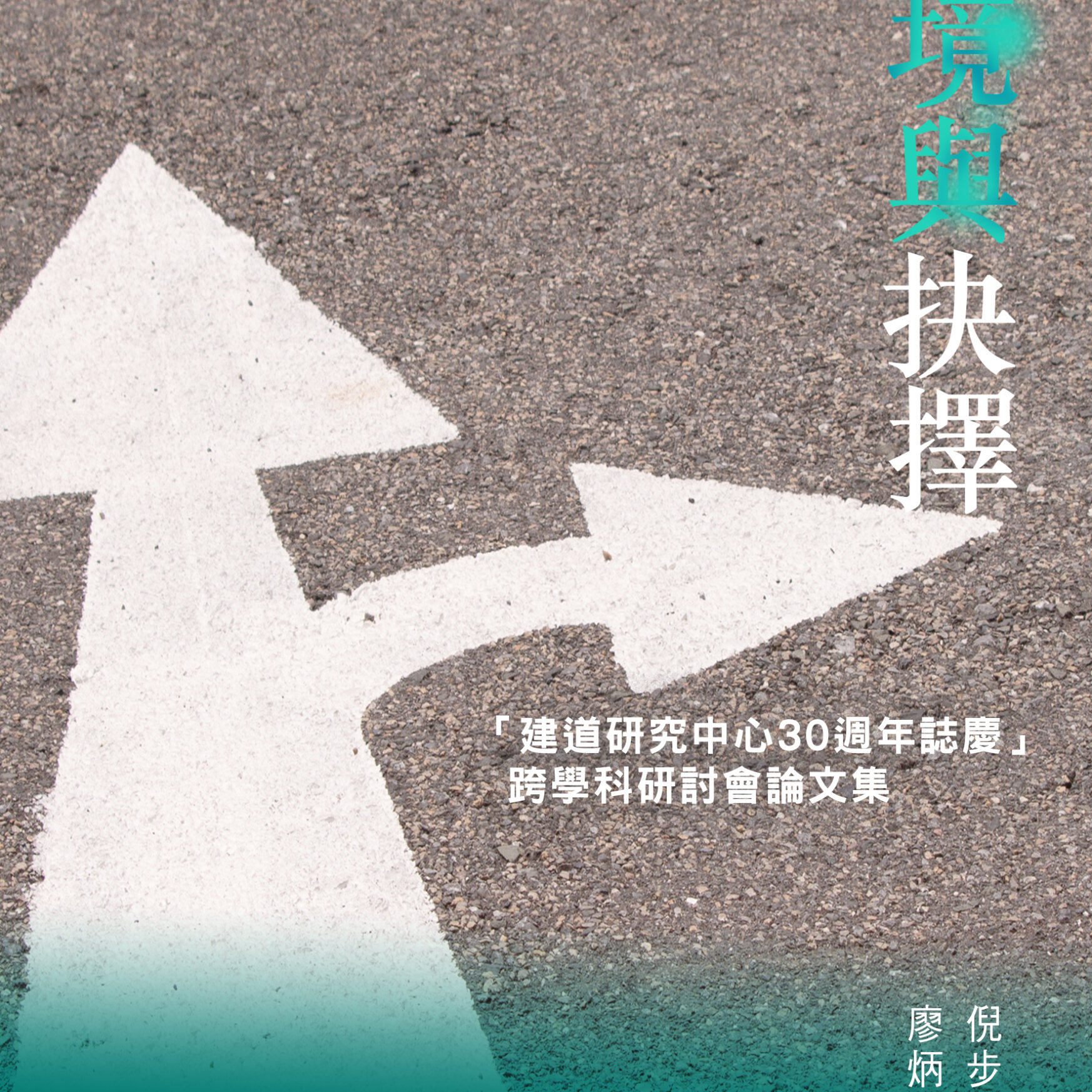建道第一屆宣教學博士畢業生
從「本土主義」到「後殖民主義」/ 周翠珊博士
對許多人而言,學術是冰冷的!但對我而言,學術研究更貼近「真實」,當中有人性、有掙扎、有無奈。我很慶幸,有機會參與在達貢巴人的宣教歷史當中。
我和丈夫到西非迦納北部穆斯林城市天馬里市宣教,一共十年,在最後的三年,「住家清真寺」的數量以眼見的速度愈建愈多,讓我萌生了進行有關研究的想法。於是在大約三年前,報讀建道第一屆宣教學博士,在老師的引導下,一步一步完成有關研究和論文。我發現天馬里市的某些地方,每十家房子就有一家住家清真寺,來自中東的傳統伊斯蘭勢力在當地,似乎希望用另一種方式體現「伊斯蘭國」,探其原因,主要和「本土主義」興起有關。
「本土主義」興起
許多人認為達貢巴人傳統信奉伊斯蘭教,但事實上穆斯林人數激增,是經過殖民政府統治,和獨立後被屬於基督教地區的南部人管治,這兩波洗禮後,穆斯林人口比例由原本的百分之二十幾兩度翻倍,不足一百年,增加到今日的九成多。最吊詭的是,穆斯林人口比例激增的兩個時期,都是宣教士最活躍的時間。宣教士在當地辦學、扶貧,很受歡迎,但基督徒數字沒有增長之餘,穆斯林比例更是一再翻倍,主要原因,是因為達貢巴人長期受著外來文化侵襲,為了生存,以及在政治以及經濟上取得更大的權力,於是結合宗教,以增強自己的「集體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而本人的論文,就是用Paul G. Hiebert 以宗教的動力學解讀的復興運動理論(Revitalization Movements),分析達貢巴族在不同時期,在外來文化入侵時產生的「本土運動」對當地宗教的影響。
「後殖民主義」
事實上,許多達貢巴人都為自己的文化而驕傲,他們亦希望可以重譜族群的歷史……有別於西方人一開始以「蠻夷之族」作為考量起始點的歷史,希望讓更多人欣賞、尊重,平等看待他們的文化。
從「宣教人」到培育「宣教人」/ 陳學文博士
當我「登陸」的那天,回顧過去,感恩的是曾經在泰國工場為主擺上,後來在香港繼續推動宣教,但神沒有叫我停下來,在主的恩典保守下,在2019年完成了神學碩士(主修跨文化)。感恩,過去我在OMF擔任差傳動員主任七年半,雖不算有甚麼建樹,但也看到幾位新同工踏上宣教工場。
為甚麼我仍要報讀宣教學博士?我寫的論文題目是〈探討華人教會如何培育信徒成為胸懷普世的「宣教人」––以美里福音堂和浸信會懷恩堂為研究案例〉,我看到香港的宣教士人數已經有670位,為此感恩,然而,宣教士的平均年齡從49歲提高到53歲,而61歲到71歲或以上的人數,從2019年的62人增加至2022年的91人,這反映出未來五年陸續會有為數不少的宣教士將要退休(以法定退休年齡65歲來定義)。過去,我在OMF有機會教導「宣教六法」,深明不是只有踏出去的宣教士才參與宣教,每個門徒都是神所使用的「宣教人」,因此,我透過〈「宣教人」的聖經神學基礎〉、〈歷史中「宣教人」模式的探討〉來奠定研究的基礎,從而論述〈「宣教人」的塑造〉,更以馬來西亞的美里福音堂和台灣的浸信會懷恩堂的實踐來參考他們如何培育「宣教人」,也透過文獻參考本港的作法,更透過實例舉出「宣教人」在宣教事工上的各種參與,最後提出教會「宣教人」培育實踐方案獻議,並大膽提出對宣教研究者進一步研究的獻議作為全文總結。
原載於《建道通訊》218期,2025年1月,頁11。
作者簡介
最新文章
新手牧者研究計劃(三):新手牧者的身心靈狀態 / 盧慧儀
2025 年 11 月 19 日
個體與關係:滕近輝思想中「深化」的靈性觀 / 倪步曉
2025 年 11 月 18 日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之起源和發展史/陳智衡
2025 年 10 月 20 日
编辑精选
[電子書]困境與抉擇:「建道研究中心30週年誌慶」跨學科研討會論文集/廖炳堂、倪步曉主編
2025 年 1 月 2 日
從梧州到長洲:建道神學院125年的挑戰與恩典 / 陳智衡
2023 年 10 月 1 日
微小教會的見證/高銘謙
2023 年 6 月 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