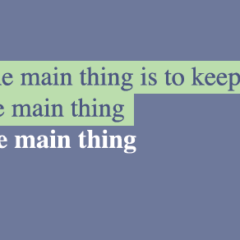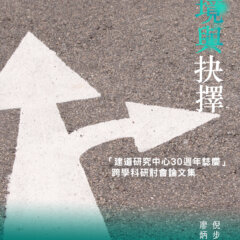從前線到神學院:改變你事奉生命的旅程 / 採訪:董智敏

Q1:Benny,知道你在讀神學之前已經是全職事奉,請你先簡單介紹自己•
「我大學畢業後便加入了福音機構全職服待,做學生工作,大約有十年的時間才進入神學院讀書。」
Q2:Benny,有甚麼令你在那個時間想放下前線事奉,到神學院全時間讀書?或者要問,為何當年自己不直接入神學院讀書?
「那時候我覺得有些事奉不一定要讀太多神學,有些事奉崗位未必需要太多神學知識,並不是說讀書不重要,我是很喜歡讀書的人,只是青年人需要大量的陪伴和同行的時間,你只需要比他們多行一步便足夠了,這些未必需要讀神學。這是我當年的想法。
當事奉一段日子,我開始發現有些不足夠的地方。在我的事奉年日遇上2014與 2019年,當時發生太多的事情,學生們都希望你能夠給予一個說法,又或者你身邊會聽到許多聲音需要去分辨。這個時候,我發現自己的不足。
另外,在帶學生小組的時候,我經常都要帶查經或者分享,實踐了許多,但我並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得合適,沒有一些有經驗和有份量的人告訴我可以怎樣改善和進步,自己需要有好的導師和老師來幫助。
當然,最後決定讀神學是因為看見一個更大的禾場和需要。因為學生都會繼續成長和進入教會,所以除了學生工作外,我都會想到整體教會的牧養需要,怎樣才可以幫助到教會不同群體的需要。所以我都放下前線的青年工作,到神學院裏裝備,希望日後可以有更廣闊的服待。」
Q3:當你進入神學院讀害後,對你的事奉生命,心志有甚麼影響?
「有一個階段,事奉的人會覺得教會未必做得好好。在神學院讀書時,我會了解不同教會的需要,對於教會的困難,有了新的角度去剖析,其實好多時候不是教會的錯,其實我們都有份去造成教會的問題。可以說,討論問題的人有很多,但願意一起認真去建立教會的人卻不足夠。
進入神學院讀書,可以幫助自己校正事奉觀念,代替只是批評教會的不是;而且,我發現在不容易的環境下建立教會是更重要的。其實,這幾年讀神學是幫助我的事奉生命,少了一種「只在言語上」的批評,多了「行動實踐」去建立教會。這是我一個明顯的改變。
事奉心志方面,我有更廣闊的看見。昔日自己十分集中做青少年,現在看見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崗位事奉,有些人做敬拜事奉好好,有些人適合做研究,教會的長者亦需要人照顧等等。
讀神學的時候,老師都給了我一些提議,例如:功課主題不要做青少年,試一試做其他群體;例如:我常常帶青少年門訓,若我做成年人門訓會怎樣呢?我比青少年年長,帶門訓可以直接教導他們,若我帶成年人或長者門訓,會變成怎樣呢?自己因而多了許多想像。
在實習教會,我為一個成年父親做初信栽培,他的兒子都十七歲了!跟他溝通的時候,我才發現他是這樣看兒子,有時候我會夾在中間,聽一聽兩方面的想法,這些都給予自己有更廣闊的思考和心懷去作牧養的工作,甚至以一個家庭的整體去看牧養,而不只是從青少年的角度去看教會牧養。」
Q4:在你讀神學時,有沒有刻意去一些群體實習,從而擴闊自己?
「第一年我在實習教會做青年和成人工作;第二年比較特別,我去做傷健群體,這是我從來沒有接觸的群體,香港教會亦不多會做這些事工。過去,我印象中教會信仰都傾向知性多一點,但面對智能不強的群體,又或者他的身體情況不容許他做一些實踐,那信仰對他們而言是甚麼呢?這給我很多反思!原來信仰可以如此簡單直接,這拉寬了我對信仰的想法。除了神學家給予我們新的思考角度可打破一些思考框框,原來前線服侍,去跟不同群體的接觸,都一樣會打破自己信仰的框框。」
Q5:你經過幾年學習後返回之前服待的福音機構事奉,自己覺得有甚麼不同之處呢?
「一方面現在的崗位不同了,主力做同工培訓;另一方面,因著有不同前線經驗的整合和理論的基礎,所以,讀神學後,我更有信心以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去處理前線事奉所面對的挑戰。有時候可以给予中肯的意見和協助。
此外,因著在神學院的學習,我建立了一個事奉群體的網絡。過去,我只集中做青少年,現在可以聯合不同的教會和牧者一起事奉,我自己的事奉視野和禾場都開闊了許多。」
Q6:如果今日有一個年青人來到你的面前,他剛剛大學畢業,有心事奉,你作為過來人,曾經闖蕩江湖,你會給予他甚麼意見呢?
「唔⋯…現在事奉與讀神學有許多模式,有些可以一邊事奉,一邊在神學院尋找合適的支援和課程進修。我會先了解他的負擔和感動,還有他生命的階段與處境,然後一同想像他可以怎樣行。但最重要,還是看神的呼召。」
Q7:現在你已經神學畢業,為何繼續一邊事奉,一邊仍然進修神學?
「一方面,現時的信徒都有很好的神學裝備,例如基督教研究碩士的課程,所以我都希望自己在神學裝備上有更豐富的學習和更有深度的思考。
另一方面,亦涉及自己事奉的方向,做訓練同工的崗位,自己亦需要有更好的神學裝備。」
原載於《建道通訊》219期,2025年4月,頁16-17。
最新文章
專訪——潘仕楷老師(下集)/ 訪問及撰稿:李蕾
2025 年 5 月 16 日
專訪——潘仕楷老師(上集)/ 訪問及撰稿:李蕾
2025 年 4 月 29 日
【代院長的話】把重要成為重要 / 高銘謙
2025 年 4 月 1 日
编辑精选
[電子書]困境與抉擇:「建道研究中心30週年誌慶」跨學科研討會論文集/廖炳堂、倪步曉主編
2025 年 1 月 2 日
從梧州到長洲:建道神學院125年的挑戰與恩典 / 陳智衡
2023 年 10 月 1 日
微小教會的見證/高銘謙
2023 年 6 月 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