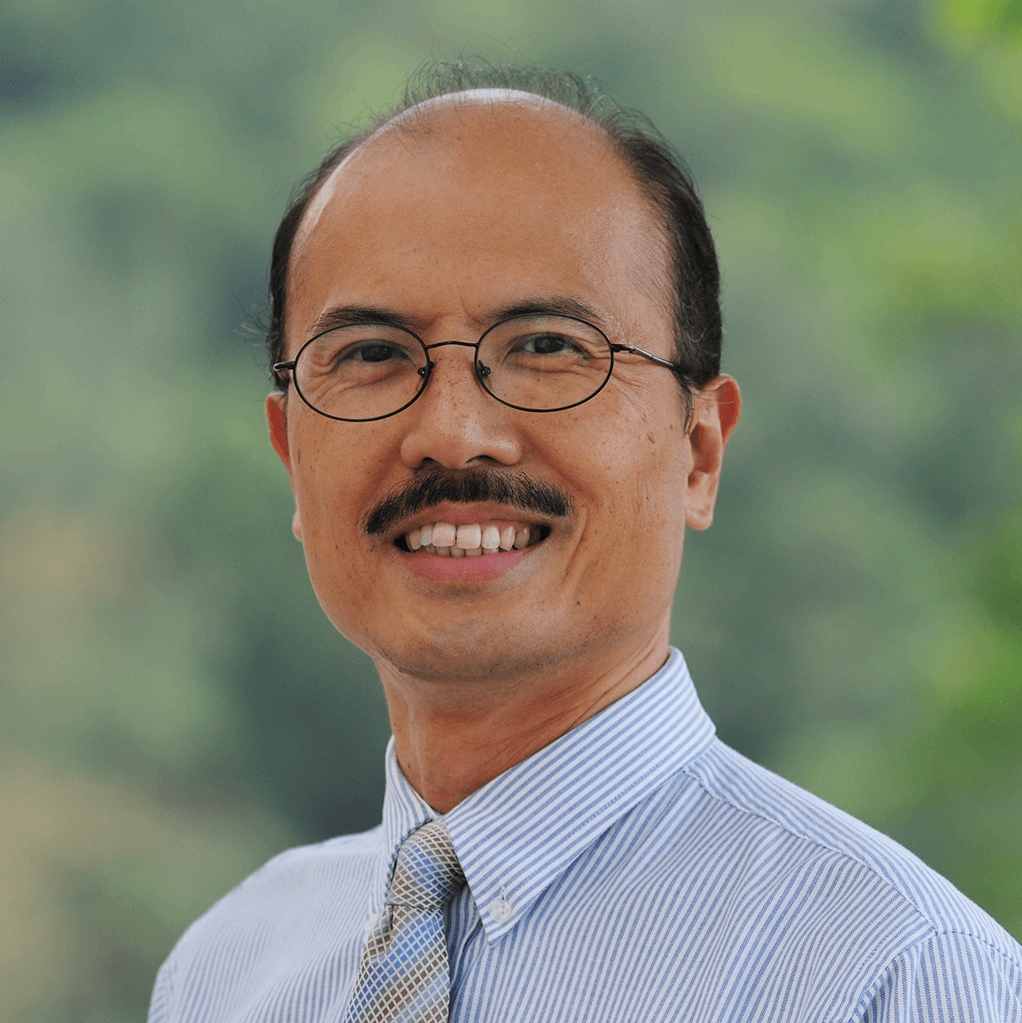由新約神學想起 / 張雲開
新約神學作為一門學問只不過兩百年左右的歷史。這並不是說,在此之前的教會從未有人反省過新約中的神學信息,或教會的神學體制未臻完備,未能有系統地剖析新約思想。事實上,初期教會早已體會到新約作為信仰規範準繩的重要性。面對著第二世紀出現的異端(尤其是諾斯底派及受其影響的各種說法),初期教父們便以新約的教導為依歸,為信仰辯偽僻邪。直至宗教改革時期為止,教會對新約的研究大概可從三方面的工作來描述:
第一,如上所述,新約經常被用來對付異端。新約辯道的功能,直至今日仍為教會所倚重。這當然和新約作為基督教信仰的正典有直接關連,但也和第二方面的工作有莫大關係。第二,新約成為使信仰系統化的基本工具。信仰內容的澄清、繼而成文、成為有系統的神學架構,是一般有組織宗教都必經的過程。當然,在歷史上有組織的教義訂定,往往脫離不了教會内部對信仰某部分內容的意見分歧,和外來異端的干擾,導致教會必須要面對及處理這些問題。過程中教會便產生了正統的規模。例如三一神的具體說法在新約中未有直言,是日後教會因應歷史因素,依據新約的理據而作出的正統說法。自中世紀以後,新約主要成為建立系統神學的研究對象。尤其是十世紀歐洲重新發現希臘哲學之後,新約被用以和希臘哲學思想結合,形成經院神學。第三,新約一直都是信仰詮釋的對象。希臘教父和拉丁教父都寫下了新約注釋。這注釋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並無間斷。
在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正本清源(adfontes)及宗教改革的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思想影響下,新約漸漸脫離了教會(天主教)教義神學的桎梏,成為被普遍研讀的對象。
宗教改革後,新約一度成為抗衡宗(Protestant)與羅馬天主教爭議及在教義上互相攻擊的工具。新約內容往往被雙方斷章取義,作為支持己方教義之用。新約神學在這段時期又和教義神學没多大分別。直至十八世紀,在啟蒙時期抬頭的理性主義之衝激下,新約神學終於脫離教義研究的局限,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然而,這歷史的發展有利亦有弊。理性主義把新約看成是研究的對象,也把它視為其他任何一本典籍一樣,是「評論」(criticism)的對象。所謂新約神學,在理性主義的前提下,便成了新約「宗教思想研究」或新約「宗教歷史研究」。尤有過之,當時有學者認為「新約宗教」作為一個歷史現象,不能單從新約內容去理解,而必須將其置於當時各種猶太和非猶太的宗教大環境底下一併研究;以達比較和溯源的果效。很快地,新約只被視為歷史文獻,是最早期教會的見證而已。在理性主義及歷史主義的大前提下,現今的信仰和新約的現象之間有著一個不可跨越的鴻溝。然而兩者之間又如何能連結在一起呢?十九世紀歐洲自由主義的答案是把新約思想道德倫理化(ethicized),而二十世紀的作法是把新約非神話化(demythologized)、實存化(existentialized)、和相對化(relativized)。即使新約學者中基督徒大不乏人,而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亦曾興起所謂「聖經神學運動」,當中好些學者想結合新約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和新約作為歷史上教會認信的內容這兩方面的走向,但終因在研究方法上無法超越歷史主義的桎梏,各學派在基本假設和出發點上又無法互相兼容,加上研究成果亦未能幫助教會面對六十年代美國社會的急遽變化,整個運動在七十年代漸漸瓦解。
這一切錯綜複雜的歷史演變,對教會有很大的衝擊。其中一個較明顯的後果,甚至連華人教會都受其不良影響所株連的,就是西方較保守教會中自十九世紀以來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由於批判性思想都與歐洲學府有關,教會看見由批判性學術方法所帶來的不信和懷疑主義,於是或多或少否定了學術方法在聖經研究中的地位。至今我們還偶爾會聽見有教會表達類似的立場,說要讀聖經不需要到學校裡去唸,免得信仰受污染。這當然是橋枉過正,但也反映出過去二百年來由西方以至東方研究聖經工作的一大難題。今天學術界並無所謂統一的新約神學硏究議程,所謂新約神學,是泛指研究新約神學思想的一門學問。各有各的做,用不同的方法,採取不同的出發點,借用不同的角度去讀新約。這種百花齊放的現象能維持多久沒有人知道,但對於篤信聖經為神的默示的信徒來說,這卻並不完全是件壞事。至少我們在這個偌大的研究空間中,可以盡力做好我們的研究和教導聖經的工作。
我們千萬不能繼續採取一種被動的反智主義來讀聖經,盲目的批評所有學術工作及研究成果。顯而易見,宗教改革期間的巨人像路德、加爾文、慈運理等人,都是徹頭徹尾的學者,承襲著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的優良傳統,在哲學、文學、語言學和神學上,都有很深的造詣。他們受過正統的學術訓練,講的寫的都是深刻的、有分量的、思考過的東西,足以改變時代。教會的悲劇是放棄鼓吹並拒絕嚴謹的學術工作,而懷抱一種經不起考驗,並且陷人於更深的偏見之中的愚民主義。
另一方面,聖經學術研究亦不能和信仰脫節。就以新約為例,我們生活在啟蒙時期後的人,的確再也無法忽略新約的歷史性(historical nature),以致我們必須事注研究新約本身的信息;但我們也堅持它的歷史時刻性(historic nature),以致新約那承先啟後的本質不會被忽路,它所關注的題目,如有關終末之事(終末論)、救贖之事(救贖論)、彌賽亞之事(基督論)、基督徒生命之事(人論/教會論)等等,而它對現今世代的挑戰和警告,不會被忽略。倘若啟蒙運動帶來的最大惡果是叫人夜郎自大,無法無天地宣稱「上帝已死」;那麼基督徒的託付就是要向世界指出上帝今天仍然曉諭我們,在各樣的事情上驗證上帝的真實,成為上帝當代誠實無偽的見證人,存著這種心志作聖經研究工作,懷著這種抱負作聖經信息的宣講。
原載於《建道通訊》117期,1999年10月,頁15-16。
作者簡介
張雲開
聖經系副教授
國際學院總監
Latest Articles
新手牧者研究計劃(三):新手牧者的身心靈狀態 / 盧慧儀
2025 年 11 月 19 日
個體與關係:滕近輝思想中「深化」的靈性觀 / 倪步曉
2025 年 11 月 18 日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之起源和發展史/陳智衡
2025 年 10 月 20 日
Highlights
[電子書]困境與抉擇:「建道研究中心30週年誌慶」跨學科研討會論文集/廖炳堂、倪步曉主編
2025 年 1 月 2 日
從梧州到長洲:建道神學院125年的挑戰與恩典 / 陳智衡
2023 年 10 月 1 日
微小教會的見證/高銘謙
2023 年 6 月 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