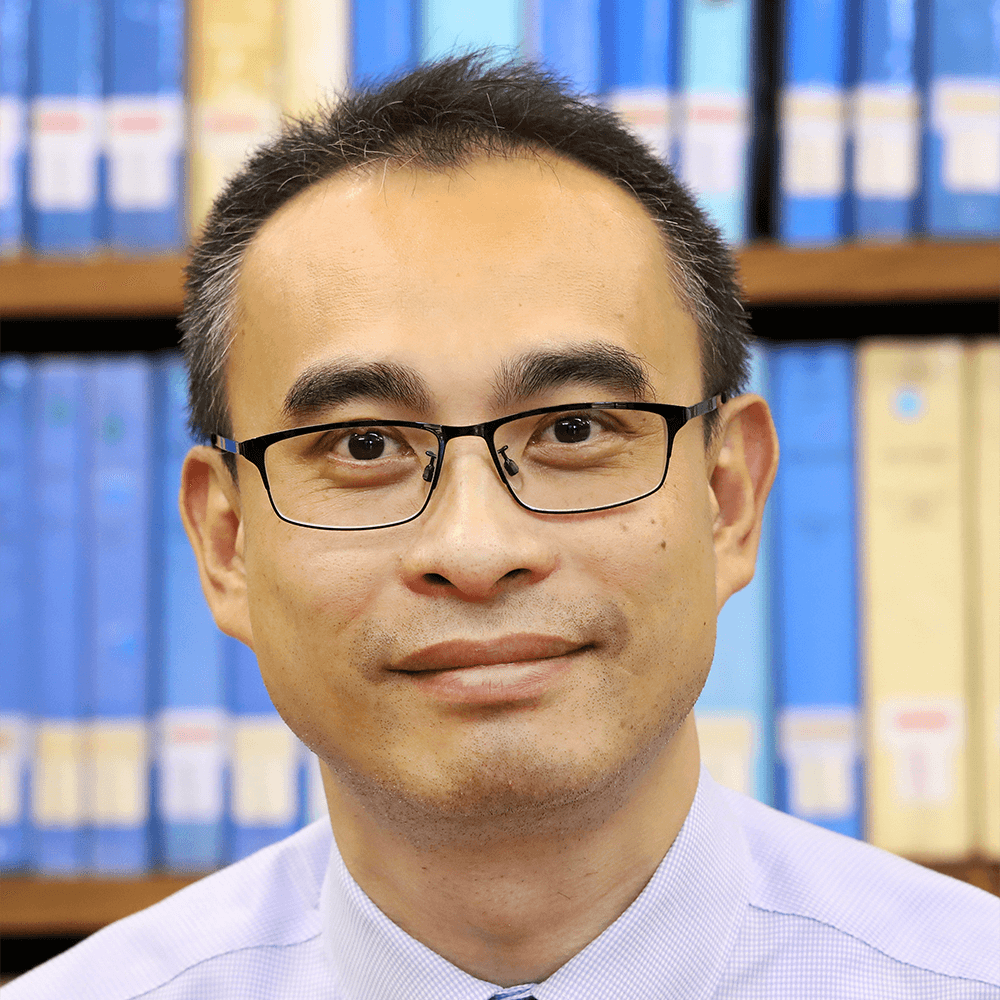【牧人視野】和平與抵抗:潘霍華的觀點(上) / 李文耀

拒絕簡化的思考
和平與抵抗(peace and resistance)看似是一組對立的觀念:不是和平,就是抵抗,我們只能二擇其一。宣揚和平的人與發起抗爭的人亦很容易在各走極端之下彼此批評、互相攻擊。要雙方冷靜下來聽聽對方的意見已相當困難,莫說取得甚麼共識或達成合一。
不過,當我們從「手段與目的之關係」(mean-end relationship)看和平與抵抗的時候,兩者又不一定存在對立。我們可以通過和平的手段達到抗爭之目的,譬如甘地(Mahatma Gandhi)的「和平抗爭」(peaceful resistance)或尤達(John Howard Yoder)的「非暴力抵抗」(non-violence resistance)。[1] 或者,我們可以通過抗爭的手段以取得和平,譬如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論「締造和平的國度」(the peacemaking kingdom)。[2] 在前一個理解裡,「和平」不一定是抗爭之目的(可爭取更平等的待遇、更人性的狀況或更公平的選舉等),它只是管理行動的一個原則、規範。在後一個理解理,「和平」是人類追求的目標,並且需要通過抗爭、「否定的否定」(negation of negatives)來促成。[3]
於是,宣揚和平的人可以有很多種類。他們可以是一羣主張採取和平手段的人,但爭取的東西、目標可以是相當功利、個人化的,跟人類共同的善(common good)無關。他們亦可以是一班促進、維持世界和平的人,卻容許「適度」的暴力、不太「和平的手段」。[4] 當中亦有人以和平、非以暴易暴的手段去化解仇恨,在世間散播和平的種子。潘霍華究竟屬於哪一類?
首先要指出的是,我們不能太草率地看潘霍華,簡單把他定性為某一種類。[5] 潘霍華有宣揚和平的一面,同時也有發起、參與抗爭的另一面。他在早期發表的言論與後期的寫作和行動也不是完全一致的。這個現象為研究潘霍華倫理學的人帶來不少困擾、麻煩。正正因為問題的複雜性,才一直有學者為此作出深入的研究和反思。[6] 過去亦有不少學者、牧者單單抽取個別的言論或行動就大做文章,不是批評潘霍華的倫理觀太過激進、極端,就是挪用他的思想來支持自己某個政治理念、抗爭行動。如此片斷式的理解和應用實在不太理想。
究竟潘霍華是怎樣的?與解釋聖經的原則相同,我們必須先有一個宏觀而全面的了解,然後才能對某個部份、片段有一個較為客觀、中肯的認識和評論。反過來說,我們亦要把眾多零碎的片段整合起來,使之成為一個連貫、有意義的大圖畫。從片段到整體,再從整體到片段,整個詮釋的循環過程需要花上許多時間和功夫。要中肯地理解、評估一個人的思想和行動,我們必須離開片段式的閱讀和應用,也要拒絕任何一個把現成的框架、主觀的印象硬套上去的嘗試。我們要認真地了解一個人,就必須謙卑下來,讓他者向我們說話。
潘霍華的和平言論
潘霍華是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或者,他是一個怎樣的和平主義者?就這個問題,學者有許多討論和推斷,到現時為止還未有一個完全壓倒性的說法。可以肯定的是,潘霍華在平生曾發表過不少宣揚和平的言論。比較明顯而又得到廣泛引用的就是他在法諾(Fanø)會議上所發表的〈教會與世界各國人民〉(“Kirche und Völkerwelt”)。[7] 在這篇演說中,潘霍華強調「和平」是上帝的命令、吩咐。既是如此,基督的跟隨者就只有服從,沒有商討的餘地。上帝的吩咐是絕對的(unbedingt),要求人不假思索地服從(blinder Gehorsam)。[8]
和平從來都不是一個選擇。上帝的旨意已通過耶穌基督清楚地表達出來:「地上要和平,因為基督在世界裡。」[9] 於是,基督的眾教會努力在世界各國人民中宣揚和平,並不覺得羞恥。和平是從哪裡來的?潘霍華不相信有一條安全的路達致和平。和平與安全是相反的,需要極大的冒險。基督徒只要相信,不求安全。有誰曉得當人們以禱告而不是武器面向侵略者時,將會有何後果呢?只有上帝知道。[10] 上帝在基督裡向世人展示出,戰爭是通過十架的路(der Weg ans Kreuz)被克服的。戰爭的號角明天就要響起。假如普世教會在此時羞於宣講和平的信息,就不能逃避由戰爭造成傷亡的罪責。[11]
另一個較多人引用的言論出於《追隨基督》(Nachfolge)。此時,潘霍華已從倫敦返回德國,在芬根瓦(Finkenwalde)主持一所由認信教會開辦的神學院。《追隨基督》正是他在神學院中教授的內容。在書中,潘霍華重申基督徒最需要知道的,便是基督在今天有何說話和吩咐(“Was hat Jesus uns sagen wollen? Was will er heute von uns? ”)[12] 在回應基督的吩咐時,跟隨者只要有簡單的信心和服從便足夠,不用經過周詳的計算或嚴謹的倫理分析。
基督對跟隨者有何吩咐呢?那就是「成為別人的鄰舍」。[13] 從降生到死在十字架上,耶穌用行動說明捨己(Selbstverleugnung)是成為別人鄰舍的先決條件。[14] 耶穌基督是世人的鄰舍,把我們的罪孽和需要擔當在自己肩頭上。耶穌基督通過捨己完成救贖,成就了和平。於是,跟從他的人也要通過捨己的實踐在世上宣揚和平。門徒就是被召去締造和平的一群人(Jesu Nachfolger sind zum Frieden berufen)。[15] 為了基督,也為了他人,門徒甘願捨棄自己的權利、尊嚴、快樂、善惡的知識、公義與暴力。[16] 如此,邪惡(Böse)就會消失。邪惡只有在遇上抵抗下(Widerstand)生存和成長。沒有了對象,沒有了抵抗,邪惡就失去力量(ohnmächtig)。[17]
從耶穌基督的身上,潘霍華看出暴力不能靠另一個暴力去解決、裁判。暴力、邪惡惟有靠捨己的實踐去化解。這是一種不訴諸暴力、抵抗的自由(im freiwilligen Verzicht auf Gegenwehr)。[18] 潘霍華同意,此種不反抗、不防禦(Wehrlosigkeit)的態度並不能被設想成一個含有普遍意義、可套用在世俗社會裡的倫理方案,因此舉只會破壞上帝在恩典下所維持的世界秩序。[19]
早於1932年12月,潘霍華在一個普世合一工作小組上亦講過類似的話。在「基督與和平」(Christus und der Friede)這篇演說中,潘霍華挑戰教會要認真面對耶穌基督在山上頒布的和平命令。作耶穌的跟隨者與作和平的見證者(Zeuge des Friedens)並不分開。[20] 再一次,我們看到簡單的信心(einfältiger Glaube)與服從(Gehorsam)的重要性。在行動中,門徒只想到耶穌基督的吩咐,並不倚靠從反思善惡而來的知識。任何人的努力,譬如通過軍事或政治的方法,都不能確保和平。人可以做的,就只有憑信心遵行耶穌基督的吩咐。潘霍華鄭重聲明,沒有服從的恩典是廉價的(billige Gnade)。[21] 耶穌基督清楚吩咐門徒「不可殺人」與「愛仇敵」。作為基督的跟隨者,教會是被召去愛鄰舍。當一個國民不聽從愛鄰舍的吩咐時,教會就要站出來為基督作見證。[22] 此時,教會要在愛裡肩負起宣揚和平的責任。
單憑這些材料,我們幾可斷定潘霍華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和平主義者。他不單以宣揚、促進「基督的和平在地上」為目標,同時也堅持採取非暴力、不抵抗的和平手段。我們要留意這些言論是發表在1932至1937年間,即是在希特拉奪權後與全面發動戰爭前的一段日子。在這個黑暗的開初期,希特拉的勢力和聲望不斷擴大,其狼子野心亦日益昭彰。納粹人員已滲透到不同的民間組織裡去,教會也不例外。在納粹意識的薰陶下,教會也宣揚「一體化」、「領袖至上」及「種族一致」等精神。一連串抵制猶太人的法案、行動在國內陸續出現。此時的德國亦開始重整軍備,並退出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23] 雖然納粹政權在壓迫猶太人和侵略鄰國上還未採取激烈的手段,潘霍華卻看出遲早將有更大規模的種族清洗和侵略行動。潘霍華在不同場合裡呼籲基督徒對上帝存簡單的信心和絕對的服從,致力在世上宣揚和平及愛鄰舍的信息。基督徒彼此間絕對不能兵戎相見,因為當他們如此相待時,就是拿著武器對著基督。[24] 假如我們的目光停在這裡,潘霍華明顯是一個絕對和平主義者。
不過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當我們把潘霍華一生發表過的東西與作出過的行動從頭至尾看一遍,便發現到內裡其實存在許多不同的聲音、觀點和立場。這裡舉一個例子。潘霍華在巴賽羅拿擔任助理牧師時(1928至1929年)曾就「基督徒倫理的基本問題」(“Grundfragen einer christlichen Ethik”)發表演說,內文提及戰爭的問題。在潘霍華看來,戰爭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它觸及基督徒倫理的核心—愛的命令(das Gebot der Liebe)。在「不可殺人」的誡命下,戰爭與愛心明顯是對立的。那麼,基督徒可否參戰呢?原則上,基督徒不應該參戰,因戰爭如同謀殺,這是一個罪行。[25]
潘霍華認為這個理解未夠深入,忽略了人在作倫理抉擇的時候常常處於兩難之間。當戰爭發動的時候,基督徒要麼保護自己的人民(即是參戰),要麼不殺害他人(即是不參戰),其實兩個決定都可滿足愛的命令。基督徒當如何選取呢?在潘霍華看來,問題的關鍵在於「鄰舍」(der Nächste)與「敵人」(der Feind)的分別。在戰爭當中,誰是「我的鄰舍」呢?答案顯然是我們的人民(Volk),因為在上帝的安排中(göttliche Ordnung),我是在自己的家人和人民中成長的。[26] 於是在戰爭中,基督徒要先愛自己的人民,然後再愛人民的敵人,譬如為敵人的靈魂、家人及國民禱告。當自己在戰爭中被敵人傷害時,也要祝福他們。[27]
基於以上兩個考慮—愛的命令和神聖秩序,潘霍華贊成基督徒參戰,只是在對待敵人的態度上與非基督徒不同。基督徒視敵方的軍人如同自己,因他們也是為自己的人民、家庭爭戰。基督徒參戰是基於愛鄰舍的吩咐,並沒有選擇餘地;潘霍華甚至說,戰爭、謀殺也因着愛我的人民而被聖化。[28] 在這篇演說中,潘霍華提出責任的重要性。基督徒不是通過訴諸良心或律法的字面意思去證明自己的行為是對的,乃是透過實踐上帝的旨意:在一個具體的時刻中,我願意把個人自私的意願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下,作負責任的人。[29] 在戰爭中,基督徒要根據愛的命令作出負責任的行動,以實踐上帝的旨意。如此看來,基督徒在維護家人和自己人民的大前提下還是可以作出抵抗,甚至殺害他人的暴力行動。潘霍華真的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嗎?(下期待續)
註釋: [1] 彭須強:《公民抗命三巨人:甘地、馬丁路德.金、曼德拉》(香港:亮光文化,2014),頁18-27;尤達著,廖湧祥譯:《耶穌政治》(香港:宣道出版社,1990),頁52-55,97-100。 [2] Jürgen Moltmann, Ethik der Hoffnung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10), 52. [3] 李文耀:〈矛盾與共融:莫特曼論教會的本質和使命〉,《建道學刊》第26期(2006年7月),頁107-27。 [4] 在筆者看來,支持「正義戰爭理論」(Just War Theory)的人屬於這一類別。 [5] 過去就有學者嘗試把潘霍華定性為「絕對的和平主義者」(absolute pacifist)、「暫時的和平主義者」(provisional pacifist)、「有條件性的和平主義者」(conditional pacifist)、「好戰的和平主義者」(militant pacifist)或「教會的和平主義者」(churchly pacifist)等。 [6] 這裡暫且舉出一些近年較有代表性的英語作品:Larry L. Rasmussen, Dietrich Bonhoeffer: Reality and Resistance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5); Sabine Dramm, Dietrich Bonhoeffer and the Resistance, trans. Margaret Kohl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9); Mark Thiessen Nation, Anthony G, Siegrist, and Daniel P. Umbel, Bonhoeffer the Assassin? Challenging the Myth, Recovering His Call to Peacemaking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3); Trey Palmisano, Peace and Violence in the Ethics of Dietrich Bonhoeffer (Eugene: Wipf & Stock, 2016); Heinrich Bedford-Strohm, Pascal Bataringaya, and Traugott Jähnichen, eds., Reconciliation and Just Peace: Impulses of the Theology of Dietrich Bonhoeffer for the European and African Context (Zürich: LIT Verlag, 2016). [7] 這是一個由普世基督教會主辦的青年會議,在1934年8月於丹麥法諾(Fanø)召開,由英國奇切斯特(Chichester)的主教貝爾(Bishop George Bell)主持。潘霍華當時正在倫敦牧養兩間德語教會。 [8] Dietrich Bonhoeffer, London, 1933-1935, DBW 13, heraus. Hans Goedeking, Martin Heimbucher und Hans-Walter Schleicher (Gütersloh: Chr. Kaiser, 1994), 298. [9] “Friede soll sein, weil Christus in der Welt ist.” Bonhoeffer, London, 1933-1935, 299. [10] Bonhoeffer, London, 1933-1935, 300. [11] Bonhoeffer, London, 1933-1935, 301. [12] Dietrich Bonhoeffer, Nachfolge, DBW 4, heraus. Martin Kuske und Ilse Tödt (Gütersloh: Chr. Kaiser, 1994), 21. [13] Bonhoeffer, Nachfolge, 67. [14] Bonhoeffer, Nachfolge, 79. [15] Bonhoeffer, Nachfolge, 107. [16] Bonhoeffer, Nachfolge, 108. [17] Bonhoeffer, Nachfolge, 135. [18] Bonhoeffer, Nachfolge, 136. [19] Bonhoeffer, Nachfolge, 138-139. [20] Dietrich Bonhoeffer, Berlin: 1932-1933, DBW 12, heraus. Carsten Nicolaisen und Ernst-Albert Scharffenorth (Gütersloh: Chr. Kaiser Verlag, 1997), 233. [21] Bonhoeffer, Berlin: 1932-1933, 233-34. [22] Bonhoeffer, Berlin: 1932-1933, 234-35. [23] 國際聯盟(簡稱「國聯」,LN)是《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簽訂後組成的國際組織,以減少武器數量、平息國際糾紛及維持人民生活水平為宗旨,全盛時期擁有58個會員國。資料取自《維基百科》,下載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8%81%AF%E7%9B%9F (下載日期2016/7/14)。 [24] Bonhoeffer, London, 1933-1935, 299-300. [25] Dietrich Bonhoeffer, Barcelona, Berlin, Amerika, 1928-31, DBW 10, heraus. Reinhart Staats und Hans Christoph von Hase (Gütersloh: Chr. Kaiser Verlag, 2005), 336. [26] Bonhoeffer, Barcelona, Berlin, Amerika, 1928-31, 337. [27] Bonhoeffer, Barcelona, Berlin, Amerika, 1928-31, 337. [28] Bonhoeffer, Barcelona, Berlin, Amerika, 1928-31, 338. [29] Bonhoeffer, Barcelona, Berlin, Amerika, 1928-31, 340.
原載於《建道通訊》185期,2016年10月,頁12-15。
作者簡介
李文耀
張慕皚教席教授
候任副院長 (學術)
教務長
Latest Articles
新手牧者研究計劃(三):新手牧者的身心靈狀態 / 盧慧儀
2025 年 11 月 19 日
個體與關係:滕近輝思想中「深化」的靈性觀 / 倪步曉
2025 年 11 月 18 日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之起源和發展史/陳智衡
2025 年 10 月 20 日
Highlights
[電子書]困境與抉擇:「建道研究中心30週年誌慶」跨學科研討會論文集/廖炳堂、倪步曉主編
2025 年 1 月 2 日
從梧州到長洲:建道神學院125年的挑戰與恩典 / 陳智衡
2023 年 10 月 1 日
微小教會的見證/高銘謙
2023 年 6 月 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