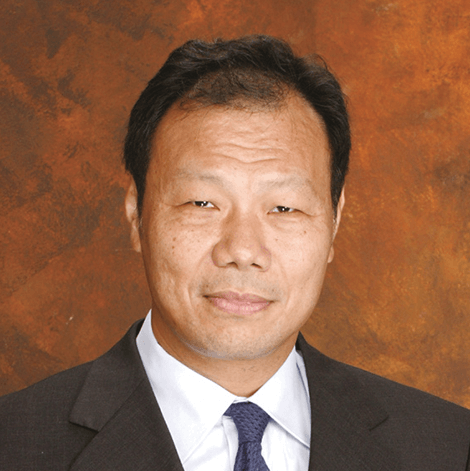【院長的話】天天冒死的事奉——寫在學院第一百屆畢業典禮前夕 / 梁家麟

為召命而事奉
2010年6月28日,學院差遣第一百屆畢業生到廣大的福音禾場去。
曾有細心的人問:111年的歷史,才有一百屆畢業生,那尚餘的六、七屆到哪裡去了?答案是:撇除頭數年未有正式畢業生外,戰爭顛沛流離的日子,以及倉猝遷港後的轉折時間,都沒舉行畢業典禮。缺漏了畢業典禮的年份,都是學院經受磨難考驗的時期。
感謝上帝的恩典,百餘年間,學院未嘗完全中輟。無論環境如何惡劣,總是有忠心的教師守護著這所小小的學院,千方百計地維持傳道人的培育工作。在物質匱乏、性命遭到威脅的日子,各人逕自逃難已不容易,要護送師生家眷遷徙,盡力保證他們的安全和供應,難度不可以想像。林道亮師母便是在一次日軍轟炸中不幸遇害,既殉國難又殉院難。我相信,守護學院的教師,除了具備信心和勇氣外,對上帝的敬畏和召命的謹守是更重要的。上帝既將我們召來,便會負責到底;祂沒叫我們撤退,我們便不敢擅離崗位。
沒有人為一份工作捨命,只會為召命而擺上一切。
建道神學院由一群為召命擺上自己的教師帶領,矢志訓練領受了召命,同樣願意為召命犧牲一切的傳道工人。百餘年的歷史記錄,可以總括為這兩句話。
劉福群前院長恆常掛在口邊一個「食雞」的教導,正好反映這個概括。他說傳道人要常存三個準備。第一是準備好為主而死;第二是準備好食雞;第三是準備好講道。
先說第二和第三項。昔日物質條件沒有今天般豐富,除過年過節,餐桌上不會有雞作菜餚;但傳道人到每個地方事奉,信徒都會熱情接待,殺雞宰鴨宴請他們,所以常常有雞可吃。至於講道嘛,信徒大多假設傳道人心中有道,不用事先準備,任何時間都會要求他們開口講道。
建道同學對這個教導留有深刻印象。每當突然被要求站講台,譬如原定講員臨時不能來,或教會有某個突發性需要,便戲稱「要食雞」了。他們將第二項和第三項混在一起說,如此臨時頂替講道便等於「食雞」。這個隱語在華人教會流行甚廣,發源地是長洲建道神學院。
劉福群院長說的第一點卻是最重要的:傳道人得常常預備為主而死。這般壯語今天已少人再說,聽來略有不合時宜的感覺。我們已鮮會視傳道為需要全人擺上的職事,鮮會要求獻身傳道者有捨棄一切的決心。不過是一份工作罷了,哪用這樣煞有介事,說轟轟烈烈的話。
我們有強烈的專業意識,卻缺少被上帝選召的認定;我們常常尋問自己的獨特恩賜與可扮演的角色,卻罕問哪裡是我葬身的工場、哪些是我得為之捨命的羊群——「十字架」正好是這兩個問題的代號。
傳道人是特殊的一群
耶穌說:「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門徒。得著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著生命。」(太十37~39)
無疑耶穌基督的話是指著門徒說的。理論上,所有基督徒都是基督的門徒,都得兌現上述經文的要求,聖經不存在僅作信徒不作門徒的選擇;但實踐上,耶穌的話卻是特別針對那群向祂宣稱「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將來我們要得甚麼呢?」(太十九27)的門徒說的。理論上,每個人都得變賣所有的來跟隨主,每個人都該任憑死人埋葬死人;但實踐上,上帝只選召了部分門徒靠福音養生,他們因福音而作眾人的僕人(林後四5),並且成了一臺給天使和世人觀看的戲。
早期教會尚未有正規神學教育和嚴謹的聖職制度,但專職與非專職的分別,有特殊聖召與沒有的差異,卻仍是清清楚楚的。並非所有參與福音工作的人都被差遣及接受按手禮。今天即或傳道人與信徒之間存在廣泛的灰色地帶,卻不因此便將兩者混為一談。傳道人是一群與別不同的基督門徒,他們的身分和職事可以因時代轉變而有增補,卻不能給取締或泯沒掉。保羅這樣表白他的身分和使命:「特因上帝所給我的恩典,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作上帝福音的祭司,叫所獻上的外邦人,因著聖靈,成為聖潔,可蒙悅納。」(羅十五15b~17)
上期《建道通訊》裡〈建道的使命宣言〉一文刊出後,有弟兄問我:「你是否反對今天坊間討論得甚為熱鬧的職場神學?」
我的回應是:對鼓勵信徒在工作與生活裡更有效地活出信仰、踐行使命,我無任歡迎,但我對一些催促信徒作這方面努力的論說略有保留。我是加爾文的學生,服膺改革宗神學,同意改革宗對「信徒皆祭司」的解釋在許多方面都較敬虔主義的更為可取,也認同社會和文化等領域都是有待攻克的信仰戰線。但我相信徹底泯除屬靈與屬世的客觀差異的神學模型,有其無法克服的內在缺憾,便是無法突顯事物的價值與工作的優先次序。要是做傳銷的和做傳福音的同樣神聖,在家裡陪孩子做功課的跟在貧民窟的服事的等值,則絕大多數人都不會捨易取難,自找麻煩。若是一切都可以神聖,便等於沒有神聖這回事。泛神聖化與泛世俗化同義。
宗教改革後三百年內,更正教鮮有推行普世宣教使命,這較強調特殊聖召(特別如耶穌會等修會)的天主教落後最少五百年。更正教最早參與海外宣教的是受敬虔主義影響的莫拉維弟兄會。這些事實並非偶然發生,卻跟當時期流行的神學理念分不開。
要是所有職業都無本質上的區別,做甚麼都是等值,那為甚麼還有人要離鄉別井,拋棄家人,捨棄家當,投身宣教開荒工作?為甚麼有人要接受微薄的薪俸,每個晚上外出探訪,犧牲自己的家庭幸福來成全別人的家庭幸福?怎麼我不可以既留住高薪厚職,又維持平衡生活,僅在工餘撥冗參與若干堂會或機構的事工?
不同職事的價值差異,真的僅決定於個人的心態嗎?只要自覺是為主而做,便做甚麼也一樣神聖嗎?要是可以將一切外在價值抹平,僅餘主觀主義的區分,則信仰實踐便無非是自編自導自演的心理遊戲了。神學不就是心理學了?
我在前文特別批評了玩弄詞彙的做法,這是將一切特殊性都抹平的拙劣把戲。在公司裡做個好僱員便是「織帳棚的宣教士」,那還需要有人到未得之地拓荒宣教嗎?這兩種都叫「宣教士」的人果真只有織帳棚與否的差異嗎?保羅是自行織帳棚的人,那留在香港拒到非洲的信徒,便更活出保羅的榜樣了,需要弟兄姊妹奉獻支持的宣教士,才更低人一等了。長宣與短宣若僅理解為時間上的差別,則我們便不要設想在這個時代尚能產出翟輔民、包忠傑、簡國慶、梁得人了。
預備為主死
建道以訓練全職的傳道人和宣教士為主要職志。我們將全職傳道的訓練跟信徒領袖培訓嚴格區分,拒絕視前者為後者一個簡易的延續訓練。所有「牧職學位」(pastoral degrees)都不能以部分時間或遙距方式修讀,更不能單靠上課做作業修足學分便獲得學位。屬靈操練與群體生活是牧職教育兩個不可或缺的元素,沒學分的要求(宿舍生活、義務工作、詩班、佈道團…)跟學分要求同樣重要。
報讀教牧學位的人,都得呈交蒙召見證,並且得清楚立志不走回頭路(no turning back),學習重建個人的生活習慣,進入傳道人的生活模式。「撇下所有」是生活模式並其背後的心態,「來跟隨我」則是使命;傳道人首先是進入一個生活模式,然後才領受召命。每個傳道者都得自問:我預備好為主死了嗎?
基於這樣的召命,我們曾送出了九十九屆的畢業生。今天請看,這是第一百屆畢業學員。
原載於《建道通訊》160期,2010年7月,頁2-3。
作者簡介
梁家麟
傑出教授
榮譽院長
Latest Articles
新手牧者研究計劃(三):新手牧者的身心靈狀態 / 盧慧儀
2025 年 11 月 19 日
個體與關係:滕近輝思想中「深化」的靈性觀 / 倪步曉
2025 年 11 月 18 日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之起源和發展史/陳智衡
2025 年 10 月 20 日
Highlights
[電子書]困境與抉擇:「建道研究中心30週年誌慶」跨學科研討會論文集/廖炳堂、倪步曉主編
2025 年 1 月 2 日
從梧州到長洲:建道神學院125年的挑戰與恩典 / 陳智衡
2023 年 10 月 1 日
微小教會的見證/高銘謙
2023 年 6 月 1 日